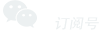

电话:0574-83071816
信箱:qxlibrary@163.com
时间:周一至周日09:00-20:00 周二09:00-11:30(下午闭馆)

从事宗教研究数十年,著有《佛寺采风——中国佛寺漫谈》《中外佛教人物论》《东来西去——中外古代佛教史论集》《当代佛教论集》《本焕长老与弘法寺》等;整理出版有《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》(共209册)《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·补编》(共86册)《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(报纸)》(13册),为近现代佛教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史料,促进了近现代佛教学术的研究。 除开展研究工作外,黄夏年十分热心中国佛教文化事业,为推动其发展做了大量工作,包括参加国内外佛教学术会议和活动,负责出版佛教会议学术论文集,策划编辑“宗教学博士文库”“近现代著名佛教学者论文集”等系列佛教学术丛书。 黄夏年为推动七塔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。2002年10月,参与制定七塔寺《文化教育事业总体策划》,2005年《报恩》发刊后,担任编委至今;2007年1月,应邀参加七塔寺“文化建设与寺院发展座谈会”,为寺院发展献言献策;2008年10月,与《报恩》原主编贾汝臻居士、圣凯法师三人协作编辑出版《七塔寺人物志》;自2017年始,接续受邀参加七塔寺举办的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演,二十多年来,数次莅临寺院举办的各类大小活动。参与寺院文化建设以来,黄夏年深入挖掘寺院发展沿革,陆续撰写数十万字与七塔寺有关的文章,先后发表《七塔寺溥常法师的振兴佛教与佛教教育思想》《中兴七塔寺的慈运法师》《桂仑法师禅修思想浅议》等数篇七塔寺史料研究相关文章,为七塔寺的史学研究添砖加瓦,意义深远。
一、学术人生四十载,促进学术界和佛教界“破壁联手”
《报恩》: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宗教研究的学术道路的?能否和我们谈谈您的家学渊源和师承。
黄夏年:我父亲黄心川(1928-2021,著名学者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)是从事宗教研究工作的,所以家里有很多宗教研究领域的藏书,我从小阅读的便是这类书籍,耳濡目染之下,逐渐也对宗教研究产生了兴趣。从事宗教研究过程中,父亲对我也有一定的指导,这些可以称作家学渊源。当然,学术研究最重要的还是靠自身努力。
就师承而言,在宗教研究的学术道路上,我有两位导师:任继愈(1916-2009,著名哲学家、佛学家、历史学家)和杨曾文(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,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)。杨曾文教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,他对我的指导很多,我受他的影响也很深。
《报恩》:您从事宗教研究工作数十年,在这几十年的学术历程中,您自身研究的重点发生过哪些转变?
黄夏年:20世纪80年代末,我在研究生期间主攻的是南传佛教。那时大陆学术界几乎没有人研究南传佛教,可以说我是最早研究南传佛教的学者之一。也正因为从事这个研究方向的人少,相对而言研究经费很不充足,受经费限制,毕业后我的研究方向就从南传佛教转向了汉传佛教。
在汉传佛教领域,我最开始从事的是天台宗研究,接着又转向了禅宗研究,再往后,出于自身编辑工作和研究的需要,又转向民国佛教和当代佛教研究。因此,佛教传入中国以来2000余年的历史,每个阶段我都写过相关研究文章。
《报恩》:您长期致力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和佛教界联合开展学术活动,您积极投身这项事业的初衷是什么?在您看来,学术界与佛教界的“联手”对佛教发展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?
黄夏年:现在看来,学术界和佛教界在佛学研究方面已经“联手”了。但在90年代初期,学术界和佛教界是处于各自独立、互不往来的状态。原因是多样的,受到一些社会思想的影响,学术界对佛教界存在一些批评,佛教界也不愿意跟批评者有过多交流,当时几乎所有寺院都没有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惯例。
当代学术界和佛教界首次合作,是1992年10月由四川省峨眉山佛教协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共同发起,在峨眉山伏虎寺举行的“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”。峨眉山虽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,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,但在此之前很少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,也没有学者去做峨眉山方向的研究工作,所以这次会议是当代佛学研究史上的一次有意义的事件。首次开展这样的合作是有难度的,学术会议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名义召开,消息发布之后还有人提出过反对意见,认为世界宗教研究所是宣传无神论的单位,怎么能跑到寺院召开学术会议?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无知的看法,但也反应了当时的舆论环境。这场学术活动成功召开后,对整个峨眉山的佛教研究和四川佛教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在峨眉山的学术活动之前,1988年我老家江苏常熟也组织召开过一场会议——“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”。那次会议是由常熟的兴福寺负责牵头,邀请学者们参与,会议主题是印度佛教。这两次会议实际上把学术界和佛教界“拉到一起了”。
让双方联合起来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?一方面,当时学术界缺少研究资金,但是有智力资本,有人才;另一方面,佛教界有充裕资金,但是人才比较稀缺。二者联合其实就是让佛教界的资金和学术界的智力结合起来,现在看来这对我国的佛学研究起到了联合助力的结果。
在我看来,学术界和佛教界的“联手”只有好没有坏,要是没有联合起来,双方都不会有今天的发展。所以,“联手”的积极意义就是推动了整个中国的佛学研究。

《报恩》:您十分热心中国佛教文化事业,整理出版有《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》《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·补编》《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(报纸)》等文献资料,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进行大量的史料汇编工作?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?
黄夏年:我的本职工作是《世界宗教研究》和《世界宗教文化》的编辑,编辑宗教刊物30多年的过程中,我阅读了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,发现其中存在一个问题:当时佛教研究集中在唐代及其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,宋代相对比较少,明清到民国阶段则更是薄弱。
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最高峰,宋代佛教也极具特色。问题在于从中国佛教发展史的角度看,唐宋时期的佛教离当今佛教比较远,当代佛教的源头不是在唐宋,而是在明清。也就是说,经由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整理之后流传下来的佛教,才是当今佛教传承的历史脉络。因此,明清到民国时期的佛教研究工作是需要加强的。
造成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是找不到研究材料,找不到材料是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多,而开展整理工作的人又太少,整理起来难度也很大。虽然当时台湾地区已经做了一些资料整理工作,但他们的工作重心是明清时期佛教资料的整理,对民国佛教文献整理的只有张曼涛编纂的一百本的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》。而实际情况是民国期间有三百种以上的佛教刊物,故而一百本丛刊并不能完全表现出已有的研究成果。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,恰逢有人愿意资助出版这些资料,借着这个契机,我就开始进行民国期刊的搜集整理工作。
做史料汇编工作,难度当然是很大的。首先,这些期刊资料不是汇集在某个地方,而是四散各处。私人收藏或寺院留存的刊物很少,大部分资料都分布在各个地方或者高校的图书馆,有些甚至被收入了善本库,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,根本无法查看。其次,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,需要对资料加以鉴别,这也有一定难度。
到目前为止,我们仍旧没有完成所有民国期刊文献的汇编整理工作,可能只完成了90%,这其实是一项需要长期做的工作。
《报恩》:在您看来,史料汇编具有怎样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?
黄夏年:整理民国时期的佛教期刊文献,其中一个价值就是梳理清楚中国佛教的发展线索。民国是跟我们当代联系最紧密的时期,了解民国佛教,有助于我们对现在佛教的发展情况做出基本判断。
民国时期,不管是学者对佛教历史、佛学文化的研究,还是佛教界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热情都十分高涨。当时的佛教发展达到了历史上除唐代外的又一高潮,短短三十多年间一共出版了300多种佛教刊物,文化含金量很高。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的佛教正处在危难之中,“庙产兴学”运动提倡把寺院改成学校,寺院不复存在,佛教不就逐渐消失了吗?这一运动对佛教打击很大。故而,当时一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寺院法师,尤其是太虚大师和有文化的法师们,积极肩负起保护佛教的责任。为了让佛教得以存续,他们到处奔走呼号,兴办大量佛教刊物,发表了很多以“振兴佛教”为主题的文章,这些文章都饱含续佛慧命的呼吁和对佛教的深厚感情。
史料汇编的第二个价值是推动佛学研究的发展。一方面,这些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之后,很多硕士、博士的研究论文就有了可供参考的材料,这些论文的发表有利于推动佛学研究;另一方面,当我们开创史料整理汇编工作的先河之后,就会有后来人继续从事这项工作,这对于佛学研究也是大有裨益。
《报恩》:想请您结合对民国佛教期刊的了解,谈谈当时的佛教刊物和现在的刊物之间存在哪些异同?在不同的历史阶段,佛教刊物承担的角色是否发生变化?
黄夏年:首先是数量上的差异:民国时期一共出版了300多种佛教刊物,但现在佛教界(包括《报恩》这类寺院内刊)所有刊物加起来约有民国时期的三分之一。
其次是内容上的差异:如果将《报恩》和民国时期出版的《七塔佛学院院刊》进行对比,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受到时代特征的影响,民国时期的刊物之间为了互相争夺社会资源和影响力,存在一股文化竞争的氛围,这也迫使期刊的内容必须各有特色。有些专门负责讲经说法,比如《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》(1937年2月创刊于江苏无锡),就是专门刊载宣扬净土宗的相关文章;有些刊物则介绍专业性知识,或刊发佛学刊物出版概况。现在佛教刊物内容更为趋同,除少数纯学术研究性质的期刊外,更多的刊物是类似《报恩》这样,以弘扬佛法、宣扬佛教优秀文化为目的,主要刊载佛学知识或短小精悍的散文。相对来说,和民国时期刊物相比,现在的刊物缺乏各自的办刊特色。
再者,就佛学院的院刊而言,民国时期的学僧相对而言受教育水平比较低,所作文章水平良莠不齐。现在学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,文章质量一定是有所提升的。
实际上,现代的佛教刊物能够长期存续的不多,有不少刊物办了几年就停刊了。可祥法师发心将《报恩》不断延续是一个很大的贡献,编辑刊物这样的事,长期做下去是很有意义的。
《报恩》:除了中国本土佛教发展外,南亚、东南亚等地区的佛教发展史也是您的研究对象,您能谈谈不同地域之间佛教发展存在的异同之处吗?
黄夏年:南传佛教(南亚、东南亚地区的佛教)跟北传佛教(大乘佛教)是不一样的,受地域文化的影响,各有特色。
南传佛教从印度直接传过去后,未进行太多本土化演变,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比较大,延续的也是印度佛教模式。北传佛教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,受到中国儒家、道家等传统文化影响后不断中国化。佛教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两千余年,与原始的印度佛教大有不同,而中国境内的原始印度佛教在一千年前就已经消失了。
佛教发展具有地域特征,是因为传教路线不同,传教过程中受当地文化的影响,发生了不同的异变。南传佛教是从南印度传到斯里兰卡,再经由印度洋的航线进入太平洋,再传到南亚、东南亚,这是一条海上传教路线,所以南传佛教是受海洋文明影响的佛教;佛教传入中国内陆走的是西域“丝绸之路”,从北印度到巴基斯坦、阿富汗,经中亚,西域,再到长安,这是一条陆地传教之路。西藏地区的佛教是在10世纪左右,印度佛教逐渐消亡时,从尼泊尔传入藏区,经过了喜玛拉雅山一线,属于高山佛教。这几条路线明显地表现了受不同的地域文化影响的特点。
《报恩》:您在上世纪末曾经发文论述了当时大陆佛学研究的一些困境,如今20多年过去了,您认为这些问题有哪些改善?从您自身经历出发,您认为现下从事佛教研究的青年学者可能会面临哪些新的难点?您有什么研究方面的专业建议?
黄夏年:我在上世纪末写那篇文章,主要是从一名宗教研究刊物编辑人员的角度出发,提出当时佛学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。上个世纪的佛学研究水平整体较低,局限于一个很小的框架,研究人员也比较少。所以当时中国佛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受海外影响,甚至有很多文章是将国外(尤其是日本)研究过的问题重新“嘴嚼”一遍,有点“拾人牙慧”。
当时我提出的很多问题,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改善。二十多年来,中国佛学研究发生了很大改变,研究实力大大增加,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。在国内,佛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,在国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;在国际上,我们已经站在世界佛学研究的前沿,现在海外召开佛学研究会议,都会邀请中国的研究学者。做中国佛教研究,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汉语是母语,国外学者则有语言障碍,这一点我们是有优势的。总的来讲,相较于上世纪末,我国的佛学研究当然是前进的,但也不能说已经很满意。
对于现在的青年学者而言,研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将中国的佛学研究与海外接轨。实际上,当下的佛学研究还是有“自说自话”的特点,全球化浪潮之下,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“出海”战略中一个重要的部分,青年学者们需要考虑如何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,和国际接轨。这要求研究人员拥有较强的外文能力,目前一些本土学者的外文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够娴熟运用的水平,而留学回来的学者外文虽然过关,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需要时间去建立和积累。
此外,学会将佛教视作一个整体,也是青年学者们需要面对的问题。我国的佛学研究,早期是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模块,后来又参照海外研究理论。西方研究是划分为认识论、宇宙论等不同的理论,西方学者是从文学、考古等不同角度开展研究,在这样的研究模式下,佛教的内容就被拆分开来。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,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佛学也是有缺陷的,所以这些也只能作为参考。
《报恩》:佛学研究的门槛较高,在您看来,对普通的佛教信众而言,学术研究的指导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?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四众修行之间的关系?
黄夏年:学术研究门槛高的原因在于它的语言要求较高。做佛学研究,首先得掌握古汉语,而且不只是具备普通的古汉语能力,佛教有很多特殊的古汉语词汇,也需要掌握。此外,研究还需要其他语言工具,最好能够多掌握一门外语。搞学术研究,没点功底是不行的。
普通佛教信 返回首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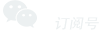

电话:0574-83071816
信箱:qxlibrary@163.com
时间:周一至周日09:00-20:00 周二09:00-11:30(下午闭馆)
版权所有 © 2016 七塔禅寺 ALL RIGHTS RESERVED. 地址: 中国宁波市鄞州区百丈路183号七塔禅寺内 邮编: 315040 电话: 0574-83071816 传真:
浙ICP备2024103791号-1 技术提供:和众互联